徐迅的散文创作始终以故乡潜山为精神原乡,通过虚实相生的意象书写和”乐水”母题的深度开掘,在城乡变迁与时代流转中构建了兼具地域特色与普世价值的文学世界,展现了散文作为”心灵史”的永恒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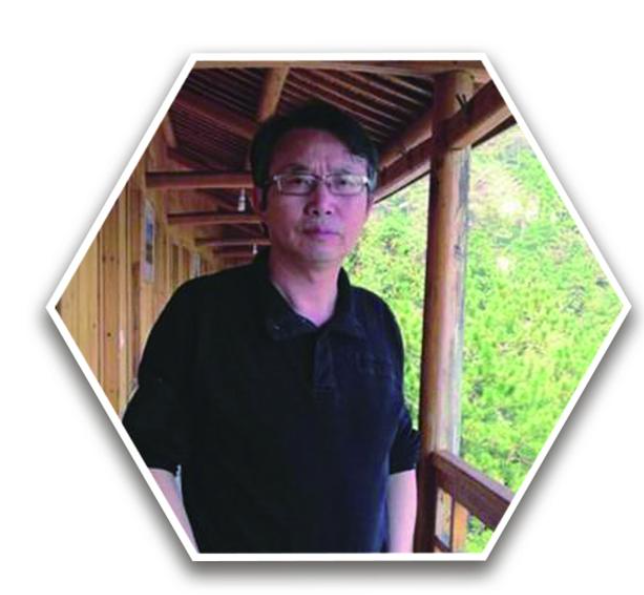
在当代中国散文创作的广袤星空中,徐迅以其独特的故乡叙事构建了一片璀璨的文学星系。作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徐迅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始终围绕着一个永恒的母题——故乡。从地理坐标上的安徽潜山到精神世界的”皖河”意象,从具象的乡村记忆到抽象的”故乡感”哲学思考,徐迅的散文完成了一场从”写故乡”到”故乡写”的深刻转变。本文将深入剖析徐迅散文创作中故乡书写的三个维度:作为生命胎记的童年乡土记忆,作为文化符号的历史地理重构,以及作为精神疗愈的永恒心灵栖所。通过对《徐迅散文年编》五卷本、《半堵墙》、《竹山可望》等作品的文本细读,结合徐迅自身的创作谈与文学评论家的观点,我们不仅能够把握徐迅散文的艺术特质,更能理解当代中国乡土散文从”怀旧叙事”向”文化叙事”的转型轨迹,以及在这一转型中,徐迅如何以个人化的诗意表达,完成了对一代人精神原乡的集体建构。
生命胎记:童年乡土记忆的文学显影
徐迅散文中最动人之处,莫过于那些饱含体温的童年乡土记忆。在《半堵墙》中,他如此描述自己的出生地:”大片的丘陵上有山、有水、有稻田,长满松树,也长满蒿子草,长满了庄稼,乡村人一年四季忙忙碌碌”,而记忆中最鲜明的感官印记是”泥土喷香”。这种对乡土气味的执着追忆,不仅是一个作家的诗意表达,更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感官记忆”——气味作为最不易被时间篡改的感官体验,成为了连接现实与记忆的最牢固纽带。徐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记录了这些感官记忆,更通过文字的力量将其转化为读者可感可知的体验,使那些从未到过潜山的读者也能在阅读中”闻到”那片土地的芬芳。
乡村人物谱系的刻画构成了徐迅故乡叙事中最富生命力的部分。《打铁的父亲》中,徐迅将父亲的形象与打铁这一传统手艺融为一体:”师徒三人浑然一体的动作又像是一个舞蹈,一张一弛,一松一紧,大开大合,也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简直是一种美的享受。”在这里,个人记忆升华为文化记忆,父亲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更成为了传统手艺文化的象征载体。同样动人的是《母亲的外婆路》中那个”拄了根拐杖,踮着三寸金莲缓缓地蠕动在田埂上”的祖母形象,她每月严格按照十天一轮回的频率在三个儿子家之间迁徙,这种固执的行走不仅展现了老一辈人的坚韧性格,更隐喻了传统家族结构的运行逻辑。徐迅笔下的人物之所以鲜活,正因为他不满足于外在描写,而是深入挖掘这些人物的生命哲学——正如他所说,故乡亲人”早已深刻地烙印在我逐渐成长的心灵上,成了我摆脱不了的生命胎记”。
童年启蒙叙事在徐迅的散文中占据着特殊位置。在物质匮乏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孩子的文学启蒙往往来自偶然的机遇。徐迅生动地回忆了小学班主任每天给学生朗读小说《追穷寇》的场景:”她读的时候抑扬顿挫,类似于’说书人’,这样就把我的胃口吊得高高的,脑海里充满了许多神奇的联想,似乎踏进了一个崭新的境地。”这种口头文学传播的原始形态,不仅培养了徐迅对语言的敏感,更塑造了他最初的叙事节奏感。而中学老师的诗词启蒙则进一步打开了他的文学视野,使他在”报纸副刊多,散文发表快”的80年代初期,迅速找到了文学表达的出口。值得注意的是,徐迅对这段文学启蒙的回忆总是与乡土环境紧密相连——是乡村教师的淳朴热情、是县文化馆小报的亲切包容,构成了他文学生涯的起点。这种将个人成长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叙事策略,使他的散文既是个人的生命记录,也是一代乡村文学青年成长的社会学样本。
乡村日常诗学的构建体现了徐迅对故乡记忆的艺术提纯。在《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中,徐迅这样描写乡村老人:”皱纹宛如屋檐上生满绿锈的青苔,上面摇曳着荒草。老人头发花白,牙齿脱落,身边斜靠着一根锃亮的竹拐杖,那样子像是一部接近尾声的黑白电影里的旧镜头。”这种描写超越了单纯的怀旧,而是通过诗意的比喻和电影化的镜头语言,将日常场景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生存图景。徐迅特别擅长捕捉乡村生活中的”微小史诗”——打铁、打豆腐、熬糖、制陶、造纸等传统手艺,在他的笔下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人类与物质世界对话的艺术形式。这种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能力,使他的散文在众多乡土叙事中脱颖而出,既避免了滥情的怀旧,又超越了民俗学的冰冷记录,达到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和谐统一。
记忆与遗忘的辩证法是徐迅处理童年素材的深层思考。在《道是故乡即家乡》中,徐迅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观点:”对于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如果说家乡是嵌入记忆深处的老屋,是童年以及老屋周围的一切,是实体,是具象的,那么故乡这个词便稍显虚饰,里面就有一种情怀,就有生命情感的外泄”。这种对”家乡”与”故乡”的概念区分,揭示了记忆的选择性本质——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完整的过去,而是经过情感筛选、符合当下心理需求的片段。徐迅的散文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正因为他把握住了这种记忆的普遍机制,他的文字既是在记录个人记忆,也是在为读者创造一种”替代性记忆”,使那些没有相似经历的读者也能通过阅读获得情感上的归属感。这种记忆的共享与传递,正是文学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
通过对童年乡土记忆的文学显影,徐迅在散文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宇宙——这里有具体可感的地理坐标(皖河、天柱山),有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父亲、祖母、乡村教师),有丰富细腻的感官体验(泥土的气息、打铁的声音、蒿子草的味道),更有对记忆本质的哲学思考。这种多维度的叙事策略,使徐迅的故乡书写既是个人的生命记录,也具有了文化人类学的普遍价值。正如他自己所言:”每一次对故乡的习惯性的凝望,都让我感到我与故乡、与故乡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亲情里深深浸透的那种人性的疼痛、隐忍和希冀”。这种凝望,既是回望过去的怀旧,也是面向未来的建构。
文化解码:历史地理的诗意重构
当徐迅的笔触从个人记忆转向潜山的历史文化长卷,他的散文便展现出更为宏大的叙事格局。在《竹山可望》这部最新散文集中,徐迅完成了一项文化壮举——将天柱山麓的这片土地从地理概念升华为文化符号,通过”诗史互证”的独特方式,为故乡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文化谱系。这种从”写故乡”到”故乡写”的转变,标志着他从抒情散文家成长为文化散文家的关键跃升。徐迅的故乡叙事不再局限于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将自我作为观察视角,将故乡作为文化样本,在微观与宏观、历史与现实、文学与学术之间架起了诗意的桥梁。
历史人物的当代对话是徐迅文化散文的鲜明特色。《悬崖上的人生》堪称这种书写的典范之作。在这篇散文中,徐迅以北宋文学家王安石、黄庭坚、苏轼以及明代大儒胡缵宗等人与舒州和石牛古洞的关系为着墨点,”或写实,或想象,或诗史互证”,让这些历史人物从典籍中走出,与当代读者进行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徐迅笔下的历史人物不是冰冷的史料符号,而是充满矛盾和张力的鲜活生命——他为官为文的精彩人生与政治上的”悬崖”处境形成了深刻的命运反讽。这种书写方式最震撼的效果是,石牛古洞的”那些石刻、那些字、那些人仿佛一起走了出来”,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记载,而成为可感可知的现实存在。徐迅以”崇敬的情感为他们’走在悬崖上的人生,延续了一种生命的永恒'”,这种对历史人物的温情凝视,既是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开掘,也是对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重构。
女性命运的文化考古展现了徐迅散文的性别视角与人文关怀。《建安年的女神》以家乡三位女性——刘兰芝、大乔、小乔的命运悲剧为线索,在”诗词、史传、话本、小说、戏曲、遗迹以及传奇故事中孜孜探寻”,还原了被浪漫化叙事遮蔽的女性苦难史。徐迅敏锐地注意到,这些”乱世里的美神”形象”也曾被血泪浸泡过”,他从地方志、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的缝隙中寻找被主流叙事忽略的女性生命痕迹,将”女神”还原为有血有肉的真实女性。这种对历史中女性命运的关注,使徐迅的散文在厚重的文化质感之外,更增添了一份难得的性别敏感与社会关怀。当他写道”这富有诗意的女性形象也曾被血泪浸泡过”时,不仅是在为历史女性发声,也是在质疑那些将女性苦难审美化的传统叙事模式。
文学意象的文化谱系学研究体现了徐迅的学术视野。《唐宋朝的马》一文对唐宋诗词中”马”的意象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从情感角度将其归类:”在大唐盛世,’马是一首诗,一首英雄自喻的唐诗。’在南宋,’马就如满弓的箭,时时都在弦上。’是’铁马'”。徐迅一连赏析了25首诗词,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马的意象与精神象征,这种将文学赏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写法,显示出他深厚的学术积累与独特的阐释能力。不同于学院派的论文写作,徐迅的文化解码始终保持着散文的灵动与诗意,他的分析不是冷冰冰的学术拆解,而是充满个人体温的”创造性误读”。这种学术性与文学性的平衡,使他的文化散文既具有知识密度,又不失艺术感染力,为当代散文如何承载文化思考提供了成功范例。
方言方音的文化密码解读展现了徐迅对语言人类学的独特理解。《云端上的乡音》从潜山方言这一”小小的语言标本”入手,挖掘背后的历史层次与文化记忆。徐迅对方言的关注不限于词汇和语法,更深入到语音、语调乃至说话方式所体现的世界观。当他分析一个方言词汇时,实际上是在解读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哪些概念被特别强调,哪些情感有专门词汇表达,哪些社会关系通过语言得以固化。这种方言书写既是对濒危语言文化的抢救,也是对标准化语境下被压抑的地方意识的唤醒。徐迅深刻地意识到,方言的消失不仅是语言多样性的减少,更是一种独特世界观和情感表达方式的消亡。他在散文中所做的,正是通过文学的力量,为这些”云端上的乡音”建立一座声音博物馆。